很显然,余秀华以经厌倦了写那些被被她看成是俗不可耐的中国诗,开始写外国诗,确切地说,是写十四行诗,但是十四行诗分为意大利和英国两种,余秀华不喜欢意大利,因为意大利语虽然是世界上唱出情歌最美的语言,但是绝对不如英国的莎士比亚那样的浪漫,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意大利的故事,但是却是英国的诗歌。
我本人不习惯逐字逐句的去解读一个人的作品,容易被带到主观主义和意向思维里面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不习惯了咬文嚼字和过度解读,我只是想从另外的一个视角,去观察,也可能是窥探一个人的作品,在他或者她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抑或是遥不可及的心灵深处的秘密。

这是一首典型的英国的十四行诗,写的很唯美,也很浪漫,思想和情绪都非常的饱满,作为一个刚刚接触到这种西方的意向文学和哈姆雷特式的白描手法的余秀华来说,已经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和值得我们仔细的去欣赏一番,余秀华这首诗歌,是她转型期的重要作品,这个作品,可以作为她前后期诗歌巅峰创作的分野,早期的余秀华是冲动的,喜欢无所畏惧,但是随着她的年龄的变化,她也在逐步的走向安静,而这种安静,到底是来源于她的内心还是她的表象,可能只能在她的一些现在已经是寥寥无几的作品里管窥了,一个诗人,过多的创作实际上一种接近自杀的行为,很容易被自己的无限制的思想扩大而谋杀,最后的结果是疯掉或者自取灭亡,诗歌需要的是精炼,也就是琢磨,不要轻易的就写作,或者说创作,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不用华丽的词语堆积,你很容易就会发现自己,正在朝着诗人的象牙塔,踟蹰的前进,其实胜利就在眼前,但是很遗憾,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就如诗人和远方一样,近在眼前的你未必可以看到,但是远在天边却又触不可及!
其实语感不能简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很多人以为语感是对语言的感觉,这是不客观的。其实它是一种与生命同构、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余秀华的诗歌对语感的表现是大力张扬个性,她打击了长久以来所谓的朦胧诗和逆向诗的语感最重大的语言法则——通过意象化途径来获取语言陌生化效果。
语感首先是基于诗人内在生命冲动,充溢生命力的蓬勃灌注,是发自生命深处的“旋律”而非文化惰性。这样在貌似平淡的表面下,语感就可能携带超语义的深刻。作为质朴无华的生命呼吸,充满音响音质的“天籁”,是直觉心理状态下,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自然外化,情绪自由流动的有声或无声的节奏。生命与语感在互相寻找、互相发现、互相照耀中,达到默契互动,语感终于成为解决生命与语言结合的出色途径之一。语感体现出由客观语意共组的整体性语境。不管是客观语义或超语义所形成的“处所”,都可能指涉语境的张力和创生性意向。
余秀华显然是一个后朦胧诗派的诗人,她很可能在不经意的时光隧道里发现她前辈的那些 “幻觉”,远远无法逼近真实的对象,他们不满足诗的单纯、线性推进、隐喻结构。余秀华意识到,世界与万物永远处于一种多维时空动态的混沌关系,面对如此复杂的存在,只有祭起“嘲笑”的法宝,才可能勉强应对说不清的世界。在经历优美单纯和谐的写作模态后,余秀华一下子被抛在都市生硬的物象面前,似乎也只有投靠“颜色”,才能超越新一轮的艺术标高。而这种感觉与正统现代主义相对单纯的像喻路径迥然不同,它导致了余秀华的诗歌变得异常细屑、包缠、相互析释,盘绕,并且形成“叙说与门环”与“混沌和张狂”互为表征的一路诗风。
比较老派朦胧诗的像喻写作,余秀华多在人与自然意象的交通感应上作文章,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多为投射移情关系,较为清晰强烈,且将本来面目颇为复杂的情像、景像、理像,多做高度概括、浓缩,凝铸成某种情景理的“秀华”体,赢得了传统意义上片言旨远的鉴赏美称。余秀华在消化复杂事物、操纵复杂事物、表现复杂事物上的能力,滋长不少可供这种诗歌题材继续增殖的元素,即大大提升了现代诗的表现力和阅读功能,另一方面,由于愈演愈烈的繁缛和激烈的词语框架,亦使文本失之了读者和堵塞了流通,
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余秀华在长期这种梦幻生活的浓浓氛围里,生与死,我与物已分不出什么界限了。妄想的偏执,梦幻的当真,经常交缠一起,相辅相生,相得益彰,使意识的屏幕一直处于超现实的磁场中。再强大的存在真实,也难以抵抗这种消解性“振荡”,纷纷化成虚无或虚空。所以我推测,在她不自觉的走向深渊地狱之时,既带有某种义无反顾、偏执的决绝,又保持某种茫然、梦幻的姿态。
其实只有极少数非常态的人,才能超越常规,真知或无知地面对大限。对于她这个“脑瘫患者”而言,要么是冷静彻底透彻死亡真面目,把死亡看作是美与生命的最高境界和归宿,要么是强迫观念推之极点,最后根本不知死亡为何物。我们不清楚余秀华究竟属于前者?后者?还是不那么纯粹两者兼而有之?这个论断最初是一些有偏执狂的评论诗歌者对顾城之死下的定论,但是从个人的感官和判断来说,我觉得更适合余秀华。
余秀华是一个远远走在公众面前的极少数的所谓是破坏艺术的风格诗人,她怪异的创造力与影子般相伴相生的人格障碍,在世俗生活与艺术活动面前所面临的人格悖论,声明一下这个悖论几乎是先在的、命定的、无法克服的宿命。必须承认,有一部分天才诗人的人格、精神发育得不十分健全完美,这当然得感谢造物主,但也必须看到,少数天赋性较高的诗人其人格、精神,严重变态、分离,颇多缺陷(包括重大道德沦丧),不过诗歌依然容纳了他们,那些独特的精神财富会穿越年代和人心,而人格缺陷仅仅作为一种人生经验教训告诫于世,而历史一般都会将它淡化甚至弃置于审美评判之外。
其实现在诗歌传统的教化功能,业已转化为自娱他娱的快乐载体。是时代和大众本身,为诗歌在当下消费中,制造如此肥厚的脂肪。那是官能意义上快乐的护发素。许多诗歌从“诗言志”变成了“屎尿屁”,人们可以随时豪饮这些屎尿屁,因为已经麻木。而这些屎尿屁抑或是窗外鸟鸣在大众由衷的拥戴中,没有意识到,诗歌在功能上已完成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渗透于各式各样速配快餐文化的诗歌,你能说它活得窝囊吗?
平心而论,是流行文化“有心”利用诗歌的古老声誉和手段,给无辜诗歌涂上“投机”色彩。有时打扮得妖冶一些,令人恶心,有时轻描淡写,倒也清丽可人。流行文化奉行的是快乐原则、感官满足原则,自然远远躲避精神重负。然而,诗歌一旦溶进这般庸常的大众生活,艺术便很快失去自身界限而被生活瓦解。这,肯定要与高雅文化、精英诗歌棗以精神深刻和个性突出为追求圭皋的立场发生严重背离的。
在公众知解力普遍匮缺,审丑、否定美学、后现代基本知识尚在“蒸发”之中,余秀华的惊世骇俗肯定不会被时代拒绝,肯定不会被主流酷毙,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成为盛宴。其实天才与疯子就在咫尺之间,当第一脚跨出去时,悲剧活着喜剧便预置了劫数。这是任何极端叛逆者无可逃避的宿命。那些僵硬板结的东西,一旦被生命的充沛打散,摇曳为众多诗意散点:发光、跳跃、震颤,弥漫于自然人事周遭,不恐惧众多感性加入,意绪与经验交混、合流,然后不断凝聚、分孽、有血有肉,生命之诗变得饱涨缤纷起来以后,蚂蟥就来了。
最后的时候还是来个老套吧。
事实上任何言语都不能完整无缺的评判一个诗人。人首先的任务在发现自己,寻找自己。要找一个与自己心理气质合拍的传统。自己并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自己,在文化传统中,总是寻找与自己最有亲和力的地方。诗人讲究词藻,力求准确,想要说自己有准备的感受,我很不习惯把对诗歌的想法理论化,诗是理论的天敌。这并不是说我讨厌思辩东西进入诗歌,也不是说我没有思辩的能力。诗与思辩有一定的关系,与乏味的理论毫无关系。不是说诗人没有思辩的才华。诗总归是非理性的东西,诗与本能、觉悟、智能有关。诗是太昂贵的东西,不是超级市场能买到的东西,要经过多幺艰辛的学习和训练,要多少机缘才可能遇到灵感。诗是昂贵的东西,也是美的东西,诗也当然是心灵的结晶。
我不骂人,不批评人,对我不喜欢的,只是沉默,因为也许是我不理解;对别人的好处则很能赞美。这是我做人的方法。我决不是畏首畏尾的人。有的事情可能没想好,有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去批评。写作除了自身品格的完善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世道人心,我从来不喜欢文以载道的作家就和诗人,我崇拜求善、求德、求美的作家和诗人,对自己也有这个要求,想做好,但不敢讲做到了。我做人不敢讲,因为人是有七情六欲之人,做文就是这样,力求尽善尽美。诗是弱的,美永远是弱的,我永远站在美一边,不站在强的一边。
诗不是战斗力,弱的东西,到某些时候也可以力挽狂澜,有时也是一种力。如果说内心深层的刺痛是余秀华走向文坛的原因,那幺对这刺痛的回应就成了分判不同类型的文人的尺度:是选择活在伤口里,用伤口的开裂来喧泄和冷笑,还是选择刺痛中的完整,在完整中悲悯这因贫血而日益冷酷的世界,就成了根本的分野。前者在自闭式的躲闪中将怨恨进行到底,后者则在不可遏制的愤怒中随时准备宽恕。
成熟的诗歌写作不得不建基于某种深刻的自省,然而这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无止境的自我剖解也将意味着诗歌的终结。
诗歌很美,很纯粹。就像是横店村孕育出的余秀华一样。
生活有时候确实有一点点苦,要是觉得现在的生活苦闷,不妨读读这本《月光落在左手上》。
透过那些直白热烈的文字,你能汲取的是满满的勇气和能量。
只需一顿饭钱,喜欢的朋友,点击下方链接,即可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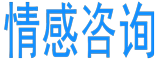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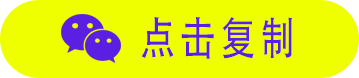




评论列表
我一直有关注,真的很有帮助
老师,可以咨询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