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作家协会主管 【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每周一、三、五更新 NO·587
贵州作家·黔山文苑
他日归乡已暮年
作者:蒋芹

一
他把头一低,迅速张开右手,五指呈内弯曲抓在脸上,手肘抵住膝盖,手指往上抻,似乎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头支撑起来,不至于让那颗被岁月催肥的头颅从脖子上断落。然后紧咬牙关,双目紧闭,上下牙因咬合而发出闷响,脸因痛苦而扭曲变形,全身瑟缩抖动。这个人 是我的堂哥。在他六十二年的过往里,他曾经九天九夜昏迷不醒,连续三个月不能发声,瘫痪在床一年半无法行走。有十年的光阴在监狱度过。又白发人送黑发人,手捧骨灰盒,亲手将自己的儿子送至坟山。
“我真的很后悔,年轻的时候太无知”他说混到今天的境地,很羞愧。
二
堂哥年轻时候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身边常常聚集着一干追随者,三五成群,男男女女。当然,堂哥并非纨绔的富家子弟,没有资格提笼架鸟,吃喝玩乐,消磨青春。他有的是年少轻狂的万丈豪情,常常在一簇簇仰慕的目光中血脉贲张,义薄云天心高涨。他有侠肝义胆的行事风格,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好打抱不平,两肋插刀,凡哥们的事,狐朋狗友的事,全都是他自己家的事。
堂哥二十三岁那年,他一个朋友的女朋友被别人拐走。在讲义气的堂哥的处世哲学里,俨然朋友妻不可欺,朋友被端了“飞碗”受此奇耻大辱,他岂有坐视不管之理?为了讨回公道,堂哥立马纠集他的一群追随者策划,拉大旗扯虎皮,信誓旦旦表示一定要去把人夺回来,不达目不罢休。甚至扬言:那家人怎么把人带走的就要让他怎么乖乖的还回来。
到了约定那天,堂哥们那一群人到了“肇事者”家里,准备好的一番义正词严交涉,本以为会全胜而归,谁料对方根本不买账,甚至还嚣张。这深深触痛堂哥伸张正义的神经,在你来我往火药味渐涨的言语冲撞间,也不知是谁先动了手。顿时,从那家人的各个房间,各道门里冲出好多人,操着棍棒,铲子、锄头,像蜜蜂一样嘤嘤嗡嗡扑出来。原来,那家人早知道堂哥们要来,暗中安插了好多人在附近埋伏着。关键时刻,跟堂哥一起去的人见势不妙纷纷逃窜,一群乌合之众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知道是对方觉得堂哥逞能,就要灭灭他的威风给他点教训,还是根本只是混乱中的一个巧合,势单力薄的堂哥被一把锃亮的锄头挖向头部,倾刻间血流如注。
送到医院的时候,堂哥早已不省人事,接诊医生判断他可能成为植物人,再无醒来的机会。最疼爱他的老母亲,天天守在床前护理,陪伴,呼喊,哭诉,不离不弃。老人家心想,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儿子孤怜怜一个人躺在床上,只要儿子还有一线生的希望,她就绝不放弃。
也许是老母亲的虔诚感动上苍,也许是堂哥自身极强的求生欲望,到了第十天,堂哥眼皮动了几次终于睁开了。老母亲喜极而泣,她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在儿子身上这儿捏捏,那儿翻翻,嘴里不停问这问那。但儿子起初没有丝毫反应,他仿佛认不得人,也说不了话。即便如此,老母亲还是看到了希望,她知道自己的儿子究竟是活回来了。从此,她更加耐心细致地呵护。她像对待襁褓中的婴儿,每天不停地和他说话,教以“妈、妈、妈”,成百上千个“妈”的强化发音,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到了第三十三天,堂哥终于能吃力地叫出一声“妈”,老人家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她继续教堂哥“爸爸”“哥哥”“姐姐”这些日常的称呼,逐渐从单个的词汇慢慢再到连贯的句子,堂哥说话的功能一天一天被重新激活,身体渐次苏醒。后来,母亲又教他走路,做康复训练,帮助恢复知觉全无的右侧肢体功能。
从咿呀学语到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从蹒跚学步到独立行走,堂哥用了整整一年半,这一年半,母亲像又重新生养他一回。到底年轻,原本有着强壮的基础体质,堂哥从最初医生断定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到能完全自理只用了一年半。上天有好生之德,堂哥受伤之深,恢复至此,已属不易。
事情刚发生时,堂哥生死未卜,他的家人都是老实厚道农村人,无力为他出头,找肇事者讨一个公道,也没有法律意识。再者,那是一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各自的家庭尚且顾不过来,谁有心思去管一个不知死活的人?堂哥当初两肋插刀拼了命去帮的朋友,忘了何为仁义,自始至终竟未去医院看望他一眼,更不要说经济补偿和体力帮助。那还是一个法制不够健全的时代,打人者逍遥法外,没有人报案,不受追究。医院住了一年半,堂哥出院时欠下外债一万多元。
多年以后,对于那场死里逃生的灾难,堂哥随身携带着两个“证书”,一个是肢体残疾证,一个是只要一开口就会被人发现的口齿不清。饶是曾有三寸不烂之舌口吐莲花又如何?事到如今,堂哥还会把“大路”说成“大度”,“见面”说成“欠面”……
三
堂哥并不是徒有其表的混事摩王。他出众的长相,灵活的头脑,极强的办事能力,良好的人际交往,曾赢得十里八村媒婆的亲睐,常常有人主动上门为其提亲。纵有东寨的佳人西坡的碧玉,可堂哥还是挑挑捡捡,不曾心动。直到出事以后,以前那些明里暗里的主动示好者,这时都避之唯恐不及。好在堂哥当时年轻,经治疗后恢复得还算好。
二十六岁那年,老母亲托人为他找了一个女子,堂哥便在母亲的催促下结了婚。也正是这门亲事,让堂哥日后痛苦不已,每每提及总是摇头叹息。
堂哥结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外面的世界商潮涌动,老家的小山村却还贫穷落后。看不到一点希望而又不甘平庸的堂哥,终有一天,辞别父母,辞别生养他的家乡,带着妻子外出,到一个外县的一个集镇上开办糕点厂,生产蛋黄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小城市一种圆圆的小小的主流糕点。
糕点厂开了几年,小地方小买卖,毛毛钱,终究来得还是太慢。逐渐还清住院时欠下的债,随着孩子降生,收入仅够糊口而已,想要发家致富似乎不可能。而堂哥是有野心的人,野心就像野草疯长,碰见野火,燎原之势不可阻挡。所以,当有人来唆使堂哥做大生意——拐卖妇女。他关闭了糕点厂,携家带口去省城,在离火车站较近的地方租了房子作为中转之地,干起了拐卖妇女的营生。
我至今没有问过,当年的堂哥态度是毅然决然还是有所挣扎,就算不从法律的层面而从人性的角度,我也认为那是不道德的。而我印象中的堂哥,是讲仁义道德和是非善恶观念的人。但没有置身其中,便无从猜测。况且,有时魔鬼和天使共存,无法区分。
事实上,改革开放为那个时代的人打开了万花筒,精华裹挟着糟粕,文明掺和着野蛮,泥沙俱下,也无情地敲开了人们原本沉睡着的金钱渴望,还原了贪婪的本质。或许,由此让原本正义正直的堂哥心安理得剑走偏锋也未可知。
从堂哥的陈述中,他在这个链条中只能算一个中层环节,他的下线从偏僻的农村带出来的女孩,每每在他设在省城的出租房住上一夜,第二日便由他带上火车,送往江西、江苏等地的农村,交给上线,卖与那些或贫困,或身体乃至智力有缺限的男子为妻。
有快钱自然也有好的物质生活,堂哥在省城的租住地每天有人进进出出,喝酒打牌,声色犬马,好不热闹。房东女主人是一位教师,可能暗中观察他已许久。一天,房东老师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蒋啊,你有一双可爱的儿女,那是你的一对宝,你可千万不要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呀”。
好心的房东是见堂哥一家人未曾做何实体生意,却能穿着体面,吃喝讲究,家里时常人进人出,便猜想堂哥有可能在做违法的事,于是善意提醒。房东一语惊醒梦中人,眼见得一双儿女聪明可爱,堂哥明白,拐卖妇女的事真不能再干了。
回到家后,他对妻子说:“我们不做了,干点正经生意”。妻子不语。
过了几天,又有下线把要“送”出去的姑娘带来了。堂哥说:“不做了”。他妻子咆哮:“人都来了,你不做我做!”。
妻子这样说,堂哥又觉得他是男人,是一家之主,要做也是他去做,而不应由女人去抛头露面。
第二天清晨,当他收拾好准备出门时,年仅两岁的小儿子从床上爬起来追着喊:
“爸爸,爸爸,我要去,你一个人去了就回不来了。”
堂哥心里一怔,立即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本能地停下脚步。可妻子和来人都不停催促着动身。堂哥犹豫片刻后,心一狠还是上路了。一路上,儿子的话不停在耳边回响,堂哥心里忐忑,好几次想打退堂鼓,可别人总劝他说:小孩子说的话,不灵。堂哥的直觉告诉他孩子的话会应验,他想退出不干,但好像又有一股令人讨厌的无法抗拒的力量在绑缚着他,他怎么也挣脱不掉,反抗不了,他不知道这种力量来自哪里,为何如此强大。最后,他怀着侥幸心理安慰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做完这一单就真的不做了。
如此,他便在心里默念了无数个“菩萨保佑”。
他幻想着平安归来,慈祥的母亲就等在家门口,张开双臂拥他入怀,给他温暖和力量,他便不再担心,不再害怕。他将金盆洗手,陪一双儿女幸福长大。
然而, 儿子的话一语成谶。
返回的途中,堂哥一行在火车站被抓。原来,买姑娘的那家与邻居素来不睦,邻居看到他家突然有个陌生的女孩进出便去报警。那个年代,一些偏远贫穷的山区买卖妇女甚为常见,当地人不用说,只凭陌生人的穿衣打扮和神态,便能判断身份是否是买来的。
警方顺藤摸瓜就这样抓了堂哥,同时,一个拐卖妇女的犯罪团伙落网。那是一个“严打”的年代,经审理,堂哥因拐卖人口被判刑十二年,被送到江西某监狱服刑。
堂哥从小很聪明,尽管脑神经受损,他的聪明依然存在。入狱后,堂哥及时、清醒地认清现实,明白任何消极避世和无谓的冲撞均没有出路。他发挥了一贯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不久便和狱警打得火热,也深得大多数同在服刑的犯人认可,混得一个管理伙食的小头目。
再后来,因表现良好获减刑三年。就这样,堂哥也还是结结实实在监狱呆了九年整,而那九年,正是堂哥身强力壮,大可干一番事业的年纪,可惜大好的青春年华不光被虚度,而且被蒙上阴影。
四
刑满释放回到家,堂哥的妻子告诉他原来积攒的十几万元全花光了,眼看着两个孩子上中学,正是需要用钱的年龄,堂哥想着还得做点小本生意。他在贵阳大营坡的一个城郊结合部看准了一块地。那年头只需搭个简易棚,卖点粉面就可维持生计。他考察了人流量,也做了概算,大约只需要两千块本钱就够。堂哥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向妻子说他的打算,可妻子听说他要钱就怒不可遏,她说什么也不肯把钱拿出来,还破口大骂,不忘讥讽堂哥:“想要钱你挑个箩筐走街串巷捡破烂去呀,一分本钱不要。”
“那时候在城区乱搭乱建根本没人管,只要有空地,要是她肯听我的话,给我点本钱,我去弄个小摊点,后来那些地方都拆迁了,我现在早发了”。每次回忆起这事,堂哥仍耿耿于怀,咬牙切齿。
如堂哥所说,他当年看中的那个地方在贵阳城区的城郊结合部,当时有很多从乡下各地进城的人就选择在那些地方,先是摆些个粉面、馒头包子、理发临时摊点,逐渐固定再慢慢做大到搭建门面。到城市扩容统一规划建设的时候,那些地方全部拆迁,诞生了许多搬迁“暴发户”,其中有好些人家还迟于堂哥好几年后才踏足的。眼睁睁看着别人发财,一直贫穷的堂哥难免陷入怨恨的泥沼不能自拔,百般迁怒当初不支持他的妻子。
受了妻子白眼,堂哥经过再次谋划,找朋友弄了一辆报废三轮,跑起了“摩的”。在跑三轮车的那些日子里,堂哥用微薄的收入支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但九年牢狱九年离散,亲情已不大如从前,“妻子不疼,孩子不亲”。他说:“无论回家有多晚,也不论天有多寒,回到家从没有一个笑脸,没有一口热饭。”
不咸不淡的日子又过了几年, 有朋友来相约去浙江开餐馆。堂哥考虑再三,这些年跑三轮实在太辛苦,风里来雨里去,年纪渐大,年轻时受的伤也常会发作,头痛,腿也时常肿痛,家却早没有了家的温情,经济上的窘迫又压得他透不过气来。那时候的堂哥急需要一种证明自己的方式,他需要挽回在家人和朋友中失去的颜面。说到底,他需要钱,需要很多很多钱,多到足以令他扬眉吐气。他答应了朋友的邀约,期待着有朝一日荣归故里,衣锦还乡。
只是,堂哥万万没想到,浙江于他,竟又是一个凶险之地。
五
堂哥在浙江的餐馆开业后,服务热情周到,收费合理,有越来越多的回头客。开业不到一年餐馆生意火爆,引来了邻近同行的忌妒。隔壁一家店的老板是东北人,堂哥的生意逐渐火爆,东北人那儿却逐渐冷清。
终于有一天,东北人纠结一伙社会闲杂人员上门无理取闹,先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占着他的桌椅就是不点餐,再就有人拦 他的门口不让客人进,百般滋扰。堂哥吃过群殴的亏,教训可谓惨痛,刚开始,他是不想把事情闹大,想要息事宁人。可怎奈他无论怎样陪笑脸,说好话,那些小混混非但听不进,还认定了堂哥就是个怂人,于是越发嚣张,到最后竟然动起手来又打又砸,把一个好好的店砸得稀烂。
眼看着辛辛苦苦的心血被毁,蛰伏在堂哥心灵深处多年的血性被点燃,隐忍之心瞬间土崩瓦解,九年改造的教训被抛向九宵云外。他终于失去理智,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抡着菜刀出去,迎着对方就砍……
受害者逆转为害人者,这次,堂哥被判刑一年。
再次出狱时,堂哥已经五十三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这次,不仅没能证明自己,妻子在他再次入狱前和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他。开餐馆之初欠合伙人的本钱还得还,没有钱没有技术更没有了年轻时充沛的体力,堂哥再也折腾不起,只得去做些薪资低廉的活。他先后给人做过保安,当过门卫,甚至给酸辣烫店里穿过串串儿。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年,堂哥靠勤劳的双手算是慢慢把账还上了,眼看着日子也渐渐好起来。可好景不长,命运似乎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过堂哥。二O一六年,堂哥五十八岁,他的儿子在河北保定离奇出车祸死亡,肇事者逃逸。
六
“都怪孩子他妈,虽然对于孩子我也有责任,但主要怪她眼里只有钱,没把孩子教育好”他把孩子的死归结为孩子母亲的贪婪。
堂哥说在他年轻时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妻子,他到浙江开餐馆前向妻子索要车费她不给,自己是向外人借的路费,然后含着泪去的浙江。可到了浙江后妻子成天打电话管他要钱,从来不问生意如何,不问是否辛苦,是否顺利。他说他第二次坐牢的时候,妻子成天泡在麻将桌上,儿子才十二、三岁,她的妻子用一根绳子将儿子和自行车拴在一个卖气球的老头摩托车上,让老头骑着摩托车在前面跑,儿子骑着自行车被拖着跟。一路从贵阳经贵黄高速公路,到安顺市区去卖气球。
堂哥说这事的时候,我的心一直在揪着,脑子里全是那个在高速公路上被“拖”着飞奔的小小少年郎的画面。那些身边呼啸而过的车流,是否让它心惊胆寒,继而麻木?那一段走街串巷在人群中卖力吆喝,或遭人白眼,或饥寒交迫的岁月,那张稚气的脸,是否写满了无助和恐惧,终至冷漠?
可堂哥根本不知,孩子是什么时候迷上了赌博,而且不可收拾。听说,在河北保定,孩子第一次赢了上百万元,如果就此收手,他不会死。但孩子不满足,他回到家,用赢来的钱买了一辆车开着又回去了,他想要赢得更多,更多。却浑然不知自己是入了虎穴,上一次赢钱脱身已让对方愤恨不已,早想找他算账,不曾想他自己却送上门。
自然,这次去没有第一次那么幸运。刚踏进保定的土地,赌场上的交锋还未来得及开始,一场诡异的车祸就已发生。奇怪的是,车祸现场居然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肇事者无影无踪。
儿子的骨灰,最后埋在了老家。由于和妻子离婚后,儿子女儿都没跟他一起生活,前妻不让他参与操办儿子的丧事,更加重了他心里的伤痛。在儿子上山的那天,他买了几条烟,一路呜咽着,跟着送葬的人群把儿子送至坟场,亲自覆了几抔土,再向帮忙的人群鞠一躬,每人发一支烟后,不等仪式结束,不等儿子的坟墓垒完,他就孑然离开了。
七
儿子死后,堂哥的前妻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儿子的死跟他们家死去的老人的墓有关。
原来,儿子遭遇不测的前半年,堂哥重新给母亲包过坟墓。堂哥此举是觉得母亲命太苦,在他还在监牢的时候母亲就已离世,老人家在世时他没有尽到孝心,母亲一辈子为他提心吊担却没享过一天清福,他觉得欠老人的太多,所以哪怕是做苦力,稍微有点钱他就想要用一种什么方式报答母亲。然而在农村,对于一个死去的人而言,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最受公认的就是立碑和包墓。
前妻找的算命先生说,是堂哥为母亲包墓的日子不好,因而为他们家带来了血光之灾,儿子的死是这场灾难的牺牲品,这一说法触怒了他的女儿。女儿和儿子从小一起长大,兄妹俩感情超过了他这个从小到大没几年时间呆在一起的父亲,所以女儿认为是他故意要害死哥哥。起初给母亲包过墓后,堂哥本来还有一丝安慰,觉得终于了了一桩心愿,压在心里多年的那块石头业已移开,他不再那么欠疚,那么憋屈。可儿子一死,算命先生的话一说出来,女儿对他恨之入骨,原本仅有的一点父女亲情也荡然无存。他多次打女儿电话,女儿不接,发短信不回,堂哥深刻体会到“众叛亲离”的滋味。
八
在外飘泊多年后,堂哥越发觉得,自己就像是那秋天的落叶树,阵阵秋风吹来,叶子纷纷落光了,只剩下一截赤条条的树干,他感受到树叶掉落时不停抽离的疼痛,最后连树干也像遭了虫蛀,从中心开始枯萎。他也仿佛看到五脏六腑就如被虫蛀的木屑般往外翻卷,卷到快要不属于自己。
他回到了老家山村,呈现在堂哥面前的老家已面目全非,二十几岁时弃之而去的老屋早已垮塌,老地基上长着几株高大茂盛的楸木树,这个季节正开着串串紫红色的花。几只乌鸦嘶叫着飞过,落在不远处的松林里。
“倘若在人死后还能葬棺木的话,那几株楸树的大小可是够作副棺材了”这个念头在堂哥脑子里一闪而过,瞬间,他涕泪横流。
堂哥说,老家埋了他的父母,还埋了他的儿子,他以前没有尽到做儿子和做父亲的责任,现在老了,他要回来,在老家筑一个窝,想父母和儿子的时候,就去坟前和他们说说话。
作者简介
蒋芹:1970年生,贵州息烽人。1992年毕业于西南林学院,喜爱传统中医,热心公益事业。有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现供职于息烽县政协。
黔山文苑
由贵州省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贵州作家·微刊》决定从2016年9月1日起,在“黔山文苑”栏目推发的小说、散文(随笔)、诗歌(散文诗)实行微薄稿酬酬谢作者。
1.“黔山文苑”推发的12000字以内短篇小说根据篇幅和质量发放稿酬为100——500元。
2.“黔山文苑”推发散文不超过8000字,根据质量和篇幅稿酬发放为100——400元。
3.“黔山文苑”推发诗歌(散文诗)根据质量和行数发放稿酬为100元——300元。
4.凡在具有“原创”功能微信上推发过的作品,请勿投寄给贵州作家·微刊。
5.在“黔山文苑”推送的文稿可推荐给《贵州作家》纸刊刊发。
6.凡投寄给贵州作家·微刊的稿子均视为自动认可以上契约条款。
7.稿费发放时间为作品推发后2-3个月(从2017年7月始实行微信支付)。谢谢合作!
精彩回顾
欢迎关注
贵州作家
文学贵州
贵州文房三宝
贵州作家·微刊
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
主管:贵州省作家协会
主编:魏尔锅
编辑部主任:黄山
编辑:何冲 魏昉 蔡国云
野老 老八 黄 勇
微信号:gzzjwx
投稿邮箱:gzzjwx@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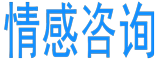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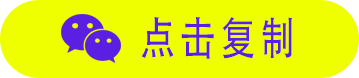




评论列表
情感分析的比较透彻,男女朋友们可以多学习学习
求助